如何阅读中国这部天书
在 海外,当代中国研究(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是一门重要的新兴学科或学术领域。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学"或"汉学"(Sinology),它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涉及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和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的研究,从国际范围内就现代中国进行的学术对话和学术竞争,现在已经吸引了大量优秀学者从事专门专业性的研究。长期以来,由 于中国社会的封闭,国际学术界无法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和调查,现代中国学实际上是"中国观察"(China Watching)或"中国猜测"(China Skeptics),而不是"中国研究",并未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往往将其研究作为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理论的应用领域而已。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现 代中国学才开始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独立的学科,世界各国学术界与中国学术界之间开展高水平的、真正平等的学术对话。由于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使得"现代 中国研究"对国际上优秀的学者更加具有吸引力。国情研究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实践基础,同时需要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那么如何系统地研究中国国情呢?这就需 要参照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提出的三条基本要求:首先,研究国内和国际现状,对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系统、周密的研究, 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把握客观的真实情况;其次,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包括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再有,学习国际理论与经验,既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也 包括极其丰富的社会科学,由此来"有的放矢","的"就是具体分析中国的发展问题,"矢"就是国际理论与经验,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这就决定了我们要从不同的层次来进行分析:
第一是实证--理论层面:首先分析中国的发展实践与国情变迁,从实践分析中抽象出理论认识,同时充分借鉴西方发展经济学成果,形成理论概括,这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多次循环往复。
第二是认识--政策层面:研究国情的目标是作出知识贡献,影响公共政策,"急国家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国情研究的最大价值就是在理论与实践认识的基础上,提出发展的目标与战略这一最大的公共政策。其中很重要的是识别出发展的挑战,这就需要发展诊断这一中间环节。
第 三是过去--现在--未来层面:这是指要从历史维度来认识国情。一是30年尺度分析,重点分析改革开放30年发展实践(1978~2009);二是60年 尺度分析,分析建国以来60年(1949~2009)的发展实践;三是千年尺度,延伸到古代中国,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国情。现状分析以及综合诊断是 对现状进行分析,目标与战略则是前瞻分析。国情研究不但需要历史感觉、历史体验、历史认识,也需要现实理解与现实参与,还需要未来愿景与未来眼光。
第 四是世情--国情层面: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环境下,我们不仅要研究国情,而且要研究世情。因为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不知 彼,则不知己。这个彼不只是对手,而是全世界。不了解世界,就无法准确地了解中国;不具有国际视角,就无法深入地认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 下,世界影响整个中国,世界改变整个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也会影响整个世界,中国也将改变整个世界。所以我们既要研究国情还要研究世情,即世界的发展动态 变化,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也提供了极大的机会。
我们所做的国情研究是属于"实证社会科学研究",主要回答:当代中国实际"是"什 么?已经或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就不同于"规范社会科学研究",即应该"是"什么,对各种行为方式的合意性作出判断。这就需要以真 实的中国为研究对象,以科学的方法、历史的观点、宏观的视野、国际的视角、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研究。这是坚持不懈的知识积累而不是断断续续的研究,是比较 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研究,是较为全面的和多角度的而不是片面而单一的研究,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深入研究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一般性描述,是采取跨学科和多角 度的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而不是仅从某一学科或方法作单一专题性研究。总之,国情研究也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 对此笔者将其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专业化研究。国情研究是非常专业化的研究领域,同时又需要将不同学科专业知识加以集成、综合和凝 炼,并从事创造性的知识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其中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是重要的办法。定量研究之所以成为一种知识贡献,是因为提供了一种我们称 作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知识。通过定量研究能够提供关于中国国情与发展史的数据、信息和知识,这就能真正深化我们对中国发展历史轨迹的理解。
第 二,开放式研究。"文革"十年、包括"文革"之前的十几年,中国的社会科学界与西方同行相互隔绝,而且封闭时间太长,正常的学术研究被政治(权力)统治和 垄断的时间太长。即使当时最优秀的学者也是十分封闭的,既不能出国进行学术交流,也基本不了解国际社会科学的发展和进展,更谈不上进入国际主流(当然是西 方学术界主导的)。社会科学上的研究方法、研究理论,不参与到主流之中,就没有办法和别人交流,同时也就没有办法对人类的社会科学知识作出同样的贡献。
第三,参与式研究。我们从事当代中国学研究,与国外的"中国观察"或"中国猜测"最大不同之处是参与式研究。这样才可能真正深入地了解与认识中国。如何持续参与研究,以下两个导向是最为重要的:
一 是发展挑战和问题导向。我们要研究现实中国的"真问题",选择中国的发展挑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论是治理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还是就业问 题、能源问题等等,都是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将把对中国的挑战视为对自己的挑战,主动及时研究对于中国的挑战,并且从研究中获得"真知"。
二是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我们要提出解决重大挑战的"真办法",及时地、前瞻性地回答如何来处理和应对这些挑战,进行高水平的发展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这就构成了"挑战-应战"研究模式,研究挑战是为了更好地应战,研究应战是对挑战的积极回应。
第 四,森林式研究。观察和研究中国既有不同的价值观,又有不同的角度。我们应当避免对中国认识的片面性,毛泽东曾说:"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 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因此,我们对中国的研究不仅要从地面近距离地直接观察各种"树木"(企业或 个人)的微观变化,而且还要从高空俯视和全面观察整个"森林"(社会和国家)的宏观变化,给出多方面总体评价。
第五,创新性研究。学术研究 就是求真与创新,发现新现象,提供新知识,提出新理论。国情研究也同样如此,它需要发现当代中国发展中特有的新现象和新特点,需要不断提供比较系统的当代 中国变化的新信息和新知识,需要创新性地提出和解释关于中国发展的基本理论和重要观点。我们以中国崛起为主题,主动回答中国崛起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它崛起的国际背景是什么,它的国内经济背景是什么,它的政治背景是什么,以及中国如何更加成功地顺利地崛起、和平地崛起、可持续地崛起、绿色地崛起。从理 论角度来看,还提出了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用创新说来解释中国的崛起。又如我们通过研究综合国力及国际比较、研究影响发展的五大资本及国际比较,从历史背景 和国际比较研究中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创新不仅要突破他人,更要突破自己,包括自我纠正。研究现代中国本身是一个信息和知识不断"搜索"的过程,需要不断认 识、识别、检验、修正和超越。
第六,集成式研究。当代中国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空前复杂多变的历史画面,她的变化与发展由各方面的因素决 定,不能从单一方面、单一学科来研究。我们采取的方法是综合研究、集成创新,这包括以下几方面集成:一是信息集成,通过数据实证来提供中国的关键性信息。 二是知识集成,集成了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环境生态等不同学科的知识,作为分析中国的综合理论依据。三是思路集成,集成了我们多年不同领域国情研究 所形成的政策思路。集成创新并非知识的简单排列组合,而是通过再加工、再组织,提高知识附加值,实现知识向更高形态转化的过程。实现这一转化的关键是要像 毛泽东同志所主张的"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明确的观点去统率材料"。这也是集成创新的"灵魂"。
中国开创 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它是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伟大复兴的创新之路,是推动经济繁荣、社会转型、中国 巨变、迅速崛起的"人间正道"。中国学者需要树立起学术自信与学术自觉,全面认识并深入研究"中国之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体系,使之成为全面 了解、真正认识、深刻分析、深入理解中国的主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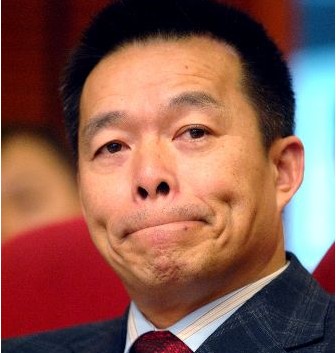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