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第四个年头,这一年,历史开创性地留下了许多极不平凡的记载:
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正式动工兴建;
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向上甘岭阵地发动强悍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坚守阵地,在43天内打退了敌人900多次进攻,歼敌2.7万,我军阵地巍然不动;
濒临破产、关门歇业的北京前门烤鸭老店“全聚德”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公私合营,此谓起死回生。
历时十月,成效显著的“三反、五反运动”宣告结束。
这一年,在中国还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建立。虽然说这个剧院在当时犹若一学步孩童,并不被广众所看重;虽然说一个剧院的建立,于当年来讲,只是微弱地闪耀于宇宙星空中的一颗星,但是,这个剧院历经坎坷,克服了种种难以数得清难以说清的困难,终于以它顽强的生命力走至今天。随着那一年北京人艺的建立,在中国的话剧圈内便相继有了以北京人艺,辽宁人艺、上海人艺为首的“八大人艺”。八大人艺很有名,也颇有实力,在话剧界占有绝对地位。掐指算来,沧海桑田60年,现如今,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独领风骚,在广瀚无际的艺术银河中,原本微弱的一颗星已演变成灿烂星空,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上具有旗帜的象征意义。那七大人艺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惨淡营生,难以常年坚持舞台演出。如此这般说来,在1952年所诞生的这个剧院,作为后来中国话剧的佼佼者与代表者,其艺术价值是无限的。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世界舞台上颇负名气,有这样的一种提法则被广泛认同,世界有四大著名话剧院:法兰西喜剧院,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莫斯科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标榜著名自有著名之道理,在舞台表现形式呈现多元文化形态的今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上述几家已逾百年历史的老剧院,依旧以创新求变的生命力量,成为世界演艺舞台上的庞然大物。
偌大的北京城,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商家老字号比比皆是,全聚德、东来顺、同仁堂、荣宝斋……驰名京华,生生不息。笔者以为,老字号未必非以百年论,就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老说,在它所走过的近60年的历史中,剧目璀璨、表演艺术家几代迭出,演剧风格自成体系,每有新剧新闻,满城争看争说。对北京人艺素有感情的画家胡絜青曾恰如其分地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国有国宝,家有家宝,一个城市也有自己心爱的宝物,北京人艺可以说就是北京的市宝。从我四周的北京市民的谈吐之中(既包括文艺界人士,也包括工人、店员、甚至街道上的老爷子、老太太们),我看出了这一点:他们看一次北京人艺的戏,就能增加一大堆聊天资本。大家聊起北京人艺来,兴趣极大,没完没了,亲昵得很,就像讨论自己心爱的宝物一样。”北京人艺,也该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京城老字号了。
有关这个剧院的故事与话题太多,上下60年,阡陌纵横,北京人艺是一本大书,是一幅厚重的历史长卷,展卷观书,跃然于纸上的分明是舞台上那一群群鲜活的文学形象,是那些如珍视生命一般创造了不朽舞台形象的艺术家们。受字数所限,不大可能若庖丁解牛般地细致,本文只是择其重点加以概述。
一
正如京剧艺术之魅力,许多人尽管无缘能一一看到她留给人世间的光彩,但提起《霸王别姬》、《四郎探母》、《群英会》来依旧是津津乐道。有不朽的京剧耆宿,则留下不朽的千古绝唱。京剧如此,北京人艺也如此。
北京人艺的开篇可追朔到1952年的6月12日。北京东城灯市口史家胡同老门牌56号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宿舍,在老式年间,这条胡同的西口曾有一座史可法祠堂。胡同得其显耀,不仅仅是这里坐落有北京人艺的演员宿舍,也不仅仅是在本院落中住着焦菊隐、欧阳山尊、叶子、沈默、舒绣文、童超、董行佶这样的导演和演员,更重要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在这里成立的。当年的北京人艺没有自己的剧场,没有像样的排练厅与办公环境,只有56号院这么个小小院落,但是建院成立大会却开得简朴而隆重。
1952年6月12日晚7时,在史家胡同56号院正式举行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大会。在不大的一个小院内,来了许多有头脸儿的大人物,当晚出席建院会的有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廖沫沙,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欧阳予倩、副院长张庚、李伯钊,北京市文联主席文学家老舍,著名剧作家曹禺,大导演焦菊隐、欧阳山尊等。小小庭院,既没有张灯结彩,也没有鼓乐喧嚣,在院子的一端摆放了几张铺着白布单的条桌和木椅,便作为了主席台。本院职工列队坐在一排排的小马扎儿上,吴晗代表北京市政府宣布批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曹禺担任院长,焦菊隐、欧阳山尊任副院长,赵起扬任秘书长。
二
北京人艺之所以是独特的,其中所具备的因素很多,她不仅仅体现在这个剧院具有着极为鲜明的导、表演艺术风格及所呈现出的舞台美术的完整性等特点,同时还包含着很重要的一点,这是一座学者型的剧院,早在1952年建院初期,从创始人“四巨头”的学历即可看出,这座剧院在建院时就已经站在了很高的文化起点上。
院长曹禺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23岁便创作发表了话剧《雷雨》,此后则一发不可收,他的《日出》《北京人》《原野》成为中国当代戏剧舞台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总导演焦菊隐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1930年,曾受李石曾的委托,创建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在他出任校长的四年时间里,培养了“德、和、金、玉”四科京剧演员,像王金璐、高玉倩、李玉茹等人均“焦氏”门下。他是中国第一个翻译苏联戏剧家丹钦科的《文艺 戏剧 生活》的人;焦菊隐主动放弃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及西语系主任的优越条件,来到北京人艺实现他一生所追寻的剧场艺术之梦。
欧阳山尊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上海大厦大学,少年时代便受到父亲欧阳予倩的影响而参加进步剧团的演出,早在抗战时期,便在贺龙领导的120师担任战斗剧社社长。
赵起扬曾经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参加主演了《白毛女》《前线》《粮食》等剧,后来他担任了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秘书、冀南区党委文委副书记等职。可以说在北京人艺建院之前,北京人艺的“四巨头”在艺术界举足轻重。
如何办一座一流水平的专业话剧院?新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究竟是什么样子?它的指导思想和建院规划是什么? 统统都没有现成的。在北京人艺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令人心血沸腾的“42小时谈话”,这就如同是俄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科,1897年,他们在莫斯科的“斯拉夫集市”饭店曾经畅谈要建立莫斯科艺术剧院。同样,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围绕着如何创建北京人艺,广开思路,海阔天空,神思飞扬,不拘一格,每个人把各自对办剧院的理想、观点统统全端到桌面上来,在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之后,最后集中形成大家所一致认可的建院方针。
首先切入的话题就是关于莫斯科艺术剧院。欧阳山尊详细地介绍了他在苏联所看到所了解的莫斯科艺术剧院,从该剧院的剧目建设、生产程序、总导演制、剧目保留制、导表演艺术的追求以及整体风格的形成,均一一做了介绍,他还介绍了该剧院创始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他的表演体系,谈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契诃夫、高尔基在剧院建设及剧本创作上的友好合作关系。
经过42小时的细致讨论,“四巨头”们一致认为,莫斯科艺术剧院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艺术上有严格要求的剧院;是一个艺术水平很高并且形成了自己艺术风格和演剧学派从而响誉世界的剧院。为此,他们确立了长远宏大的艺术理想:要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设成像莫斯科艺术院那样的一流的文化剧院。最初有一种提法,为了效仿莫斯科艺术剧院,新剧院的名称应该称为北京艺术剧院。
“开国元老”们头脑异常清醒,他们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认为这个剧院决不等同于莫斯科艺术剧院,应该特别强调剧院的人民性和大众性,应该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出发,这个剧院在制定剧目上要有一定比例地选择上演表现新生活、反映社会精神面貌的作品。曹禺曾这样回忆道:“我们四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干过戏,都对莫斯科艺术剧院有一定的向往,都有对建设一个国家剧院的设想。我们在一起长谈了十来天,我们都希望办一个莫斯科艺术剧院式的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的中国自己的话剧院,是北京的而不是莫斯科的。要办好一个剧院首先是统一创作方法,要强调深入生活,要全面学习、借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要吸收民族艺术的表现手段,同时我们还要把好剧本关和演出艺术质量关。一个剧院要有自己的保留剧目,演一个丢一个,这不是办剧院的办法。”
从曹禺的这段话中我们可悟出一个道理:虽然谁都没有办剧院的经验,但是他们在把握剧院发展的总体方向上是准确的,中国的戏剧有自己的特点,要辩证地认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虽然以莫斯科艺术剧院为追寻奋斗的目标,但决不能生搬硬套。此话这般说来,自然有其原因。上个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两党正是蜜月期,受中国政府的邀请,苏联向中国各个技术领域派出了几百个专家组。
为了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全国的话剧界、京剧界和其它地方剧种也都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大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的热潮。外来的东西不一定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你让中国的戏曲演员也去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内心体验,肯定是猴吃麻花儿满拧。而北京人艺的演员们,对“斯氏体系”顶礼膜拜,充满了神秘感,大家很迷信,也很迷恋,认为该体系是一剂药到病除之良方,可以帮助你获得“灵感”,打开创作形象的大门。1956年,苏联专家库里涅夫来北京人艺亲传“斯氏表演体系”,排练高尔基的《耶戈尔 布雷乔夫和其他的人们》,许多著名演员如朱琳、吕恩、董行佶、刁光覃、于是之、郑榕等人均参加了排练;而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起就已经开始接触“斯氏体系” 的焦菊隐先生,虚心求教,每日在排练场看苏联专家排戏。
表演领域中,体验派与体现派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始终就在打着“官司”莫斯科艺术剧院成立之后,演员注重以外部技巧为主的形式主义的表演,而这样的表演往往失之于虚假浮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根据这种现状,结合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排练,提出了表演上内与外如何统一的问题,强调内在的技巧,强调内心体验,这便产生了著名的斯氏“体验派艺术”。北京人艺建立了,好啦,到了摒除虚假的外部表演的时候了,于是许多演员怕谈体现,怕谈人物,片面地强调人物的内心,又是写人物自传,又是做无休止的案头分析,从理论到理论,分析角色的心理动作线,最高任务……结果呢,演员当进入排练时,脑子一片空白,那些企图为创造人物而服务的一系列理性的分析丝毫没有起作用。
在表演上,究竟是“从内到外”还是“从外到内”,在剧院内各有遵循,比如像黄宗洛,他在进入创作人物的初期时,总是习惯借助于化妆、道具、服装等外部手段而一步步走近人物的内心世界,逐渐达到人物形象的丰满,他的这种行之有效的“从外到内”,可从《茶馆》中的松二爷,从《智取威虎山》里他扮演的土匪黄排长,从《三块钱国币》中的警察等形象得到鲜明印证。而“从内到外”的创作方法,先是在心中培养一颗角色的种子,并逐渐化之于外,成为舞台上真实的形象,在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是于是之,他的“从内到外”,他对角色的内心体验方法,则是更为鲜明地继承了焦菊隐的“心象” 学说,他宁愿服从焦先生。于是之辩证地说:我觉得“从内到外”和“从外到内”,并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方法。在一个角色的创作中,它们差不多都是结合着使用的。
从戏剧观念的角度看,对“斯氏体系”大可不必独尊,甚至当年在俄国也存在着与斯氏体系分庭抗礼的梅耶荷德以及对梅耶荷德崇拜至极的瓦赫坦戈夫。
在当年的苏联,“斯氏体系”被神化,容不得任何怀疑,假若有人企图颠覆,比如说对莫斯科艺术剧院叛逆而去的梅耶荷德,便引来了杀身之祸。对莫斯科艺术剧院,焦菊隐充满了崇敬之情,对“斯氏体系”的研究,他也是最为关注并注入了种种思考的导演,在上个世纪50年代,焦菊隐连续发表了《怎样认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怎样运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形成过程》等一系列的文章。1953年,当剧坛国人对“斯氏体系”顶礼膜拜之时,焦菊隐便明确说道:“我们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同样不应当生硬地搬用理论和教条。应该根据他的观点、思想和方法,研究我们的生活实际和创作活动,结合着我国的情况来寻求具体的运用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它和发展它。”
在北京人艺的历史上,向以拥有一大批叫得响的剧目著称于世,深得观众青睐,这些戏的演出远可回溯到将近60年前的《龙须沟》, 这是北京人艺历史上的第一部大戏。北京人艺很幸运,建院之初,便得到了老舍先生的厚爱,他亲自到北京南城的龙须沟观察生活,创作了话剧《龙须沟》。在导演焦菊隐的带队下,全剧组来到龙须沟进行体验生活。这个戏的创作和演出,极为轰动,振奋人心。舞台上流淌着一幅幅真实生活的生动画面,演员所塑造的是一个个性格鲜活的人物形象。于是之,当年23岁,因在戏中成功扮演了鼓书艺人程疯子而大红大紫,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老舍被北京市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有意思的是,“人民艺术家”之称号空前绝后,唯有老舍先生独受此殊荣,以后再也没出现过第二位。《龙须沟》的创作和演出,使北京人艺在表演创作上,开始自觉地走着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成为北京人艺演剧风格的开端。
在话剧界,似乎有一不成文的标准,无论是一个剧院或是哪位演员,要考验你的实力或表演才华,须过一过演出《雷雨》的这道门槛。在中国,《雷雨》是演出最多的一部戏,它所拥有的观众也同样是最多的。北京人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上演“五四”以来优秀作品的剧院。作为戏剧大师曹禺的剧作,《雷雨》并不是那种简单化地反映生活的作品,每一个演员对它的理解都需要有一定的认识水平和艺术修养。至今,在许多老演员的记忆中,当年《雷雨》的排练工作既漫长又艰辛,总共用了八个月的排练时间,其中仅体验生活、做分析人物的案头工作就占去了四个多月,这在北京人艺的排戏历史上也是最长的。想象一下,当年在《雷雨》中出演角色的都是话剧圈中名望很高的演员——郑榕、朱琳、于是之、苏民、胡宗温、董行佶……《雷雨》的演出,由此奠定了北京人艺的风格,表明了这个剧院的导、表演艺术在走向成熟。
三
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北端东侧,凡是路经这里的人都能看到外观庄重大方、浅米色的首都剧场,这是北京人艺的专用剧场。在许多观众看来,首都剧场作为北京的特殊文化地标,不仅成为北京人艺的象征,也是中国话剧的精神象征。
自清以来,各路名伶麇集京城,四城内演出场所不算少,但主要是演旧剧,也就是京剧。那年月管演戏的场所叫茶园,平民百姓索性管它叫戏园子,入民国后,为显示文明又改称为戏院或剧场。历久经年,戏院遍布四城,名气显赫,像广和楼、天乐茶园、平乐园、吉祥戏院、长安戏院等,演出戏码多以名角挑班演出。但是可着北京城却没有一家专演话剧的剧场。北京人艺建院后的演出场所是在东单的大华电影院,后移师北京剧场,此剧场的前身是“真光”电影院,解放后改名为北京剧场,即现在的中国儿童剧场。
因为没有专业演出剧场,那时候,北京人艺排出了《龙须沟》《雷雨》《青年突击队》等戏,经常是到各区的俱乐部、青年宫、琉璃河水泥厂、印刷厂和大学去演出,这其中固然有送戏下厂下乡为工农演出之意,但也不可否认的是确实没有剧场,只能打游击战。
周恩来总理自1953年年初始经常来看北京人艺的演出,看完戏后他如果有时间便会到后台化妆室看望演员,这时候,大家往往都会谈到剧场问题,纷纷“诉苦”一箩筐:旧电影院舞台窄小,迁换布景困难,不适合演话剧;演员要在狭小潮湿的地下室化妆,灯光都是临时装的,太过于简陋……曹禺、欧阳山尊等人也为建院以来演出剧场的匮乏所困扰,他们和演员们都希望周总理能批准建一座演出话剧的专业剧场。周恩来和大家的心情一样,他知道,一个专业化的剧院要发展壮大,要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没有固定的专业化的剧场确实很困难,欧洲各国都有规模很大的专业化剧场,莫斯科艺术剧院之所以能形成自己的演剧风格,自成体系,独树一派,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有自己的剧场。周总理嘱咐剧院专门就建造剧场之事写个报告。
北京市政府对北京人艺急需剧场这件事极为关注,1953年1月,吴晗、张友渔、周扬联名向周恩来总理打报告,提出北京人艺的固定演出场所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有必要马上修建条件较好的一座剧场,由北京人艺管理使用,同时也可解决以后国际性演出的场所问题。
经过北京市和文化部的协调,最终拍定了方案,由文化部拨款,北京市负责选址和具体组织设计和施工,在原王府井大街甲73号生产教养院旧址上盖首都剧场。建筑师林乐义负责主持总体设计,北京人艺副院长欧阳山尊负责管理全部建设事宜。
1953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总理约曹禺、老舍、欧阳山尊、焦菊隐到中南海西花厅谈老舍新写的一部叫《春华秋实》的话剧。总理更为具体详细地与他们交换了盖首都剧场的意见,他提出,900人的容量太小,是不是可以增加到1200人。欧阳山尊认为民主德国的技术质量很先进,他建议向该国订购灯光、音响、转台、通风等设备。周总理表示同意,要求欧阳山尊回去后重新计算所需费用。过后,周总理将向民主德国订购剧场器材的报告批复给外贸部办理。
首都剧场终于在1955年落成,外观稳重,端庄典雅,其观剧环境、演出设备、技术含量乃是全国最优秀的。但是花落谁家又成一大悬案,这桩悬案自有缘由。一日,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把欧阳山尊找了去,告诉说:“首都剧场应该是能够演出各个剧种,并由各个剧团所共用,不能属于北京人艺管理和专用。”
山尊当即提出:“这个剧场是总理批给北京人艺的。”
周扬的理由听上去也很充足,“可是剧场的建筑经费是由文化部的文化经费中拨的款。”
北京人艺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去接收和使用首都剧场,好不容易为剧院争取来的剧场,只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演员们窝心,但大家伙顶多是发泄一下抱怨。盖剧场的总指挥欧阳山尊心里头窝囊。曹禺、焦菊隐感叹唏嘘,苦无良策。他们在创作上可生发出无穷的想像力,但是面对官场和行政命令,大艺术家们只能是面对现实,束手无策。
新落成的首都剧场骄傲地矗立在王府井大街上,夜幕降临,灯火通明,门前人头攒动。新剧场运营起来了,开始接待文化部邀请来的中外剧团的演出。北京人艺的戏依旧日复一日,可怜兮兮地在旧电影院里面对观众的目光和掌声,依旧随着戏码的更迭在不断地变换剧场。不久,周恩来总理又一次到北京剧场看北京人艺的戏,他问到了首都剧场的问题。欧阳山尊竹筒倒豆子,将情况如实道出。随后他代表剧院又给周总理写了书面报告,提出应将首都剧场划归北京人艺管理和使用。周恩来作了批示,明确同意剧院的意见。周恩来的决定很快得到了落实,文化部、市文化局、北京人艺几家单位经过协调,正式签订了将首都剧场划归北京人艺管理使用的协议,北京人艺从此告别了电影院。正是有了首都剧场绝佳的演出条件,北京人艺在多年演出实践中营造出了它所独有的文化演出环境,得以形成几代观众群。如果没有周总理的爱护和支持,如果没有首都剧场,很难想像,北京人艺能否会演出如此经典的《茶馆》《虎符》《蔡文姬》《带枪的人》以及“文革”之后的《天下第一楼》《洋麻将》《李白》《窝头会馆》等名剧。
四
北京人艺历经60载,从编剧、设计到导演、演员,人才济济,名角辈出,这是一个崇尚完美、追求风格统一完整的艺术群体。谈论起北京人艺,无论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它演出的戏,喋喋不休于所敬佩的大大小小的演员们,提起任何一个响当当的好演员,那都是一座高山,令人仰止,焦菊隐、刁光覃、舒绣文、朱琳、于是之、童超、郑榕……以及后来者如濮存昕、梁冠华、何冰等。的确,一提起这个剧院中的许多演员,常会自内心撩拨起一种激动。我认为,观众的这种激动,实际上是在感受着那些学者型的演员们以丰富的文学修养而创造了不朽的舞台艺术形象的魅力。
做演员不易,做一个好演员尤为不易。吃话剧表演这碗饭,演员要掌握戏剧理论,要懂得表演技巧,还要有生活,没有丰富的生活经历,想象的翅膀就张不开,飞不远。然而做一个在舞台上会思想的演员,绝难。演戏这玩意儿,有的人会比较顺利地进入正常的创作状态,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有的人做了一辈子演员,苦于无路可走,每遇新角色,如临大敌,惶惶然也。
作为一个话剧演员,能够让观众看到他在舞台上会思想,这应当说是进入了表演领域的最高境界,想象一下,这该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暗下里得下多少为人不知的笨功夫和苦功夫。表演能达到化境无我,这也如同郑板桥画竹,日挥夜思四十年,画到生时是熟时。舞台灿烂生辉,在这之前你走的所有的路,都必须是以勤奋、用心、思索、修养为前提。一叶知秋。在此不妨介绍两位在北京人艺具有代表性的表演艺术家。
于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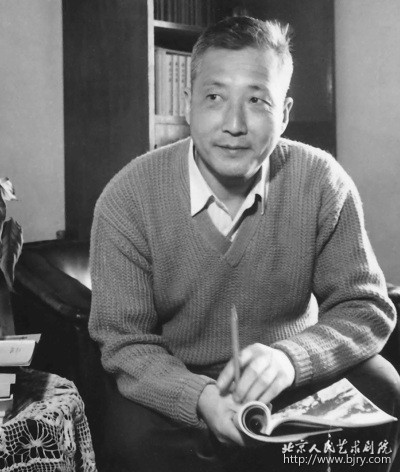
于是之肖兔,本命年,八十四岁。
电视中时常会播放话剧《茶馆》的录相及电影《龙须沟》、《青春之歌》,辛劳一生最终因穷困而自杀的老掌柜王利发、鼓书艺人程疯子、充满“小资味儿”浪漫情调的于永泽们尽管永久沉睡在了黑白胶片上,却是永远透着年轻……
话剧在中国生存只是上世纪初的事,短短的一百多年间,在这行当中,却出现了两位话剧耆宿,且同出一门,一位是于是之的舅舅,享有“话剧皇帝”之誉的石挥,另一位即是于是之,不过,有所不同之处则在于:石挥的事业灿烂于那个已逝去的年代,于是之则辉煌于新中国的舞台上。
许多仰慕于是之的人都对他怎样干上了演员这行当颇感兴趣。年轻时,于是之最初对演戏并无多大志趣,在他的理想世界中,立志想做文学家或是翻译家,做个满腹经纶、饱读诗书的“秀才”,唯独没有想到去做个闯荡江湖演戏的。他读了许多中国文学史的书,他未料到当时学的那些东西对他后来干演员有用。他说:“学语言学能使人耳朵敏锐,容易抓住别人说话的特点;学绘画能培养人的观察能力,通过人的外形特征窥见内心活动;学文学则更是提高演员素质的重要途径。”
为了最基本的生存,为了养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母亲,于是之在念完了初中后,他不得不到处去找工作,万般无奈中,他曾在日本人的仓库中做过“华人佣工”;也曾穿上一袭长衫,在衙门中某个“录事”的差,正襟危坐,抄抄写写……若不是在他17岁那年被舅舅石挥“拽”了一把,天下爱剧者也许这辈子会与于是之的名字失之交臂。
他参加了辅仁大学的业余剧团——沙龙剧团,在长安戏院参加演出了黄宗江编剧的《大马戏团》、法国喜剧《牛大王》。后来,他专门就这段经历写了一篇题为《我主演“牛大王”》的小文。短文不无幽默且带有几分伤心:演《牛大王》时,我在沦陷区的衙门里当小公务员,挺苦的。同学们看《少年维特之烦恼》,叫我也看,我看了,看不下去,告诉他们:我没有少年。
旧时,概凡学戏者,家里差不多都有点底儿,闲钱加闲功夫,若真是在梨园行中唱得大红大紫,像谭鑫培、杨小楼那样的名伶,每月挣上几千块大洋,也能置万贯家财,可话剧这行永远属于“贫困戏剧”,不仅生存丝毫没有保障,剧团也时聚时散。只有在新中国,话剧才真正获得了新生。置身其中,凡成就大业者都深知,比之“梨园”,比之影视,话剧是一门最难学通学好的艺术。其实,这行当又很难用“学”去讲通,你可以跟着师傅一板一眼地学京剧、学曲艺,学各种程式化的表演,话剧怎么学?神龙见首不见尾,师无定法,但毕竟还是有法可依,于是之在从艺之初便掌握了天下最不易却也是最容易的方法:勤奋。这是由他的出身,由对苦难历程最直接的体验所决定的。古人常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来形容一个人对事业的磨难,于是之演剧生涯的磨难何尝不是如此。
他会因一个角色的不成熟而终日萦绕于怀,坐卧不安;会因一句台词说之无味而反复揣摩;会因难“抓”住某一人物的神韵而苦恼不堪,百思欲得其解。
在中国的话剧界,于是之堪称是一位具有学者风范的艺术家。他以勤奋好学之心,多年来不断地探索和总结自己表演上的成功经验,用自己的艺术实践阐述了著名学者、北京人艺总导演焦菊隐的“心象”说,并且丰富发展了这一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他明确提出“演员应该创造出可以入诗、入画的舞台形象”。
如何做演员?是靠灵性?靠吃苦?不尽然。单靠灵性,难免会聪明反被聪明误;仅靠吃苦,而野心者也能吃得了苦。你看,于是之是如何说明白的,“演员在台上一站,你的思想、品德、文化修养、艺术水平以及对角色的创造程度,什么也掩盖不住……因此,热爱生活、爱憎分明这一条很重要。演员必须至少是一个好人:忠诚老实,敢爱敢恨,不大爱掩饰自己,我不是说随便去骂街,我是说他的心应该是透明的,他的感情是可以点火就着的——指正确的感情,不是那邪火。对生活玩世不恭,漠不关心,就不大能够演好戏。”于是之所言,词浅意厚,真实形象地表达出了做演员的道德标准。正是由于他是一位勇于勤奋探索,总是不满足于昨天的艺术家,因而他所塑造的富有生命力的舞台艺术形象,不仅具有对生活的认识价值,更具有美学的欣赏价值。
朱 旭

在演员与表演艺术之间,应该说是有一道上了锁的大门,虽无形,却沉重。每一个演员都在用毕生的精力努力想去推开这扇门,感受门内那一方充满阳光的境界。然而,无形之门却要比那厚重的紫禁城城门要沉重得多,以至令不少演员穷毕生之力却始终在门外徘徊。我所熟悉并敬重的演员朱旭,则是一位成功地推开那扇沉重之门,潇洒登堂入室的表演艺术家。
朱旭的演艺生涯的成功,其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他的表演自成一格,以喜剧的手法演活悲剧人物,令人捧腹之后又引起苦涩的回味。这是他独有的,别人学不来的。同朱旭交往,你会觉得这是个相当随和的老者,思维缜密,从容大度,语气淡而雅,笑声轻而柔,不时散发着机智的诙谐,一如他对酒的感情,味道很醇。从他丰富的笑谈及表情中,你似乎又可捕捉到影视中那一个个活着的灵魂,若隐若现,让人回味。我以为,表演风格的自成一体,是与他本人性格及心理气质截然不可分的。虽然表演的功夫乃后天勤奋而成,但生自于骨子里的那种天然而成的气质,却又是后天所学不来的。
形容朱旭的话剧表演,若以“真切感人,入木三分”形容之,倒是颇为贴切。在社会上,朱旭的名声相当叫得响,许多舞台艺术形象,由于由他演而成为永恒,很难再有人会超越他。在表现冀北风情的农村喜剧《红白喜事》中,他扮演的小学教师三叔木讷直爽,大智若愚,可气中透着可爱;在美国名剧《哗变》中,他扮演的舰长奎格,性格乖戾自信,自以为绝对正确,这与中国的阿Q精神恰恰是一脉相承。美国人在生活中常会习惯说:“你怎么那么奎格?”便指的是这种类似中国阿Q式的精神哲学。巧得很,朱旭在话剧《咸亨酒店》中曾出色地扮演过鲁迅笔下的阿Q。阿Q与奎格,一土一洋,各居东西,均同样被朱旭演得活灵活现。朱旭在退休之后,依旧恋恋不舍于舞台,在剧院上演的《屠夫》《北街南院》《生 活》《家》中出演了戏份很重的角色,人入晚境人缘更红,他的“出将入相”在北京人艺传为佳话。
朱旭凡做事都很投入,表演如此,娱乐也如此。下围棋、放风筝、拉胡琴、喝酒,此为他的四大强项。朱旭能拉得一手好京胡。当年“文革”中在干校劳动时,晚上闲来无事,便向梅兰芳的琴师姜凤山老先生学琴。本来这玩儿京胡纯属消遣之事,没成想在日后的演戏中倒派上了大用场。话剧《名优之死》中,面对千余观众,他扮演的琴师操琴上阵,弓法娴熟,丝弦起声惊四座。在电视剧《粉墨情痴》《武生泰斗》和《心香》中,这手绝活儿同样是帮了他的大忙。
朱旭的表演成功率很高,其中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即得益于北京人艺所营造的文化环境和气氛。谈到这点,朱旭颇有一番感慨:“我赶上了那个年代,进了剧院,很幸运。虽然我所走过的表演道路也不平坦,但在这个环境中融炼陶冶了人的修养,尤其是有个读书的气氛。演戏首先需讲求如何做人,如何对待生活。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文化素质不同,作品也就必然会有高低之分,文野之分和粗细之分。这些年来我演了不少的戏,也拍了一些片子,还好,能被社会和观众承认,好歹都‘混’了个奖。反过来细想,我毕竟是从那么一个人人自觉读书、自强用功的环境中走过来的……”
于是之和朱旭都共同谈到了一个在北京人艺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建立“学者型”的剧院。由于字数所限,在本文中只能将于是之与朱旭的表演艺术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典范加以介绍,其实,在这个剧院中,“学者型”的演员多得是,像郑榕、蓝天野、朱琳、童超、英若诚、林连昆、吕齐、董行佶、吕恩、任宝贤、濮存昕……在他们身上同样是相当精彩地展示了话剧表演艺术的大千舞台。
在过去了的那个比较单纯的年代里,绝然没有像今天这般来自影视的巨大的物质诱惑,那个时代里,演员拼命钻研用功,用心琢磨人物,专心演戏,心无旁骛,那是个出大演员的年代。
世界在变,中国在变,今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信息的高速传播,演员固然还是吃表演饭,而不可逃避的是,人的价值观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物质的巨大诱惑与精神上的完美追求很难做到统一。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走至今日,面对文化市场激烈竞争的现实,许多问题同样的也摆在了剧院的面前。
北京人艺的演剧生命力长久不衰,正是在于这些年来不间断地坚持演出。只有不断地拿出好戏,舞台的大幕始终是打开着,才能够得到社会和观众的认知。如何继承这座传统剧院独特的表演风格? 如何使它继续成为“学者型剧院” 的典范?路漫漫其修远兮。北京人艺今后需要走很长的路,但是对戏剧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