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提出新政治观
公方彬:自序二
《思想的原野》(上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一文在《人民论坛》杂志10月号(上)发 表后,在国内外引起远出预料之内的反响,尽管该文所涉观点只是我的《新政治 观》理论体系中的小部分,尽管编辑部为了避免影响过大而适度降调:原计划该 期只做新政治观一个专题,后来搞成两个专题;原计划请多位专家围绕我上一篇 文章——《重新诠释政治成当前最重大命题》中的思想点展开讨论,后来不具体 挑明策划的思想渊源;原计划发表我的14000字的长文,后来摘发了其中的5000 字。即便这样,由于很多人猜测此文乃中共十八大政改风向标,再加上网民和学 界高度参与,终于把一篇理论探讨或一个新理论催化成社会热点。在该文处于热 烈讨论之时,许多媒体希望我回应,而我因种种原因放弃了,但回答置疑是理论 工作者的责任,所以,讨论降温之后,在《思想的原野》出版之时,就为什么提 出新政治观,及其网上关切阐明自己的基本观点。
我为什么提出新政治观,或者说该理论形成路径和动因何在?涉及理论自身 动因,一言一蔽之,就是将政治引到平衡利益的基本功能上来,就是让政治与时 代发展同步,根本目的在于让更能满足共产党执政需要的政治理念、政治行为确立起来,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更扎实,执政能力更强。对此,已发表的相关文章已经作了重点阐述,在今后的文章著作中还要作更加深入分析。这里想换 个视角,也就是将自己长期开展理论研究的过程和脉络盘托出来,间接说明该理 论产生之必要、之必然。
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士兵的我受诸多因素影响,由文学爱好转到基层思 想政治工作研究的道路上来,最初着眼点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即寻找 僵化落后向鲜活生动转变的路径,以此改善思想政治工作者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形 象,提升工作效率,后来认识到方法手段改善而来的效力必将穷尽,必须找到突 破口。就如上个世纪80年代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由于捆住农民手脚的绳索解 除,生产力迅速释放,经济实现腾飞,农村面貌迅速改变。及至因解放而来的生 产力穷尽,农村经济进入较长期的停滞,后来将突破口选在创造生产力。这样的 规律和特征反映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就是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挖掘和激发其 主动性和能动性,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增长点和突破口,这样我就把通过个人修 养提升精神境界,产生精神力量作为自己研究的着眼点和着重点,期间不仅发表 一系列相关文章,还围绕“人生十个修养”到各地作报告,直至走上央视。尽管 演讲报告备受欢迎,尽管央视播出后获很高收视率,尽管以此内容为核心的《与 青年谈人生》出版后获国家图书奖项,我还是很快终止了这方面的工作,原因在 于过程中一个问题突出出来。
诚然,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都必须重视并提升人文素养、品德修养,问题 在于修养过程中该坚守什么,为什么坚守,怎样坚守,如果走偏怎么办,特别是 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情况下,我们甚至不知道何为最根本的价值追求。疑惑与思考 把我的研究引向核心价值观,试图通过价值坐标的确立和恒久性元素的获取,矫 正和支撑起我们的品德修养。提出核心价值观的命题应当说是个人理论研究上的 一大突破。虽然作为哲学命题,核心价值观很古老,作为企业文化命题,也是改 革开放之初就自西方引进,但作为一个政治属性命题,一个囊括了中华民族的核 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作为一个 国家和民族精神建设的系统工程提出,这在中国还是首次。至于其中有的研究成果很快进入决策,就更值得自豪和骄傲。我曾经认定核心价值观将是自己理论研究的归宿。然而,在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人们逐渐把研究重点转 移到核心价值观上来之时,我发现自己的研究遇到瓶颈,因为更深层且具决定性 的命题待解,这就是政治需要重新诠释,新政治观需要确立。
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至今,已有六年时间,期 间理论界一直努力争取突破,也就是产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甚至引起决策 层的关注乃至参与,结果仍未如愿。有人认为十八大报告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 因为提出了12个概念,其实这仍然是阶段性成果,尚不能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特征是凝练易记,突出精神元素, 具有操作性。很显然,12个概念24个字只能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 基础,而不能认定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意义上,12个概念关照了方方 面面,是对基本价值元素的集纳和归类。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西方的核心价 值观就清楚了。西方早期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博爱”,目前的是“民 主、自由、人权”。北欧国家增加了“公正和互助”,如其国会建筑的核心价值 观是:“民主、自由、平等、奋进”。以此对照,显然不能说12个概念就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在核心价值观问题上获得共识那么难?瓶颈何在?表 面看是多元价值观并存致使难以达成共识,其实更主要的还是社会主义自身内含 外延尚未获理论突破,高度依附社会主义本体理论的核心价值观自难产生。甚至 还可以说,究竟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哪个更能实现“建设 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的目标,都有研究的空间和余地。一切的一切,都决定于 我们对政治的诠释,或曰新政治观能否产生出来。不能对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生态 作出准确判断,不能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特质,就不可 能产生科学恒久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我由核心价值观研究转到新政治观研究的 主要原因。当然,真正开展新政治观研究后,发现其关照范围更宽阔,意义更重 大,核心价值观已经降至其内容之一,甚至不是决定性内容。完全可以说,新政 治观直接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实现第三次飞跃,十八大报告明确的政治体 制改革将走向哪里和走多远,中华民族是否真正实现伟大复兴。
为了阐明新政治观具有广泛关照力,这里仅就中华民族道德建设作出分析。当代人最焦虑的问题之一是社会公德不彰,为什么一个重道德甚至依靠伦理道德 维系政权与社会的国家和民族,道德建设如此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 农业经济基础上的熟人道德进入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下的陌生人道德,却尚未实 现有效转换;其次,儒家伦理下的重私德到市场经济下的重公德,尚未实现新的 平衡;再次,善和道德奠基于宗教,我们试图摆脱宗教而以政治来推动,却尚未 有效诠释和畅通路径,等等。尤其是以功利的政治解释无功利的道德和善,其间 有哪些问题需要处理,以免发生冲突?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需要开展的工作更 多,问题是表面现象背后涉及的是对政治的重新认识,也就是新政治观的支持。 否则,政治越发力,越是无法接近所期望的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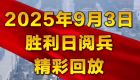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