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提出在沿海优先发展的基础上,向沿海支持内地发展的“第二个大局”转换,这个转换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张富泉:中国历史上曾有合纵连横之说,合纵成为连横的基础和先导,连横才形成大一统的强大格局。邓小平在论述“两个大局”战略及其转换时提出:“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里,邓小平用了“反过来”这个很重的词,旨在强调“两个大局”战略寓有前后相依、相辅相反的“悖理”。既然内地大局战略是沿海大局战略的“反过来”,就必须实行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的大反转,即在东、中、西纵向区域基础上合纵连横,构成沿海帮助内地共同发展富裕的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渤海横向趋同俱乐部区域。
记者: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渤海分别包含哪些省区市,为什么说是同一起跑线上的横向趋同俱乐部区域?
张富泉: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纵深的内陆,地理特点呈西高东低之势,生产力水平则由东向西呈反向梯次分布。其经济区按纵向划分呈同质性且非均衡发展的特点,而按横向划分则呈集聚性且相对均衡协调的特点。可见,邓小平“两个大局”改革开放的战略思想,完全切合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特点和基本国情。其沿海第一个大局梯度推移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就凭借了东、中、西纵向区域非均衡特点;而内地第二个大局战略构建区域协调互动的发展机制,无疑需在东、中、西纵向区域基础上合纵连横,分别构建以珠三角城市群横向连接长江中上游,包括粤闽桂琼湘鄂赣渝云贵川藏12省区市的泛珠三角经济区;以长三角城市群横向连接黄河中上游,包括沪苏浙皖豫陕甘宁青新10省区市的泛长三角经济区;以环渤海城市群横向连接黄河下游和华北东北等地,包括京津冀晋蒙辽吉黑鲁9省区市的大环渤海经济区。
对这三大横向经济区,若对照中国地图直观地看,泛珠三角、泛长三角与大环渤海都成带状分布,都有各自的出海口和起龙头作用的沿海城市群增长极与纵深的内陆经济带,要素优势与禀赋优势异质互补性极强,属典型的内聚性经济区。特别是这三大横向区域改革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均衡,财政经济规模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平均水平基本相当,资源禀赋与经济要素等发展条件也不相上下,可谓中国特有的一组内聚性趋同俱乐部区域,也是一种天然的均衡性区域资源的新发现。因此,按照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转换“反过来”的路径,将以省级为主的东、中、西纵向区域无序竞争,整合为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一组趋同俱乐部区域的均衡性竞争,即如马克思所论述的通过起点公平以及规则公平而达致终点的公平(毛程连等,2003),则可形成统一市场与公平竞争的秩序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最终完善,顺利实现区域非均衡发展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转型。
记者: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作为中国特有的均衡性区域资源,还要看采取怎样的区域政策开发利用。您认为实现更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
张富泉:财政政策是经济政策的核心。实施邓小平“两个大局”改革开放战略,始终离不开对地方参与经济的财政改革诱致性政策。事实上,沿海第一个大局战略的成功实施,关键就在采取省级财政大包干及后来的分税制。进入新世纪,转向实施内地第二个大局战略,仍需期待完善分税制改革的再突破。因为自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体制,是建立在原有省级财政承包制的基数上,其计算地方财力的方式仍然沿用着按财政供养人口计算的传统办法,随着经济发展和地区差距拉大其矛盾与问题也日渐显露出来。这正如邓小平谈到发展起来的问题所强调的:“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经济开始发展起来后,问题也开始多了起来。比如,地区差距拉大、地方市场分割、资源环境不堪重负和竞争失序、贪腐滋生等问题越来越多。这些问题集中起来,矛盾的焦点还是财政再分配问题。因此,用发展来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要深化财政改革,改变按财政供养人口计算地方财力的传统作法,实行与国际接轨的按真实统计常住人口即“标准人”分配地方财力,在这一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实现分税制改革的再突破。
记者:分配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为什么您只提完善分税制改革,并强调要由“财政供养人”向“标准人”转换?
张富泉:初次分配系市场行为,就应让市场去自主调节。其实,在这方面政府也很难有所作为。比如,中等收入阶层是多了还是少了?职工工资高些好还是低些好?这些问题都不宜过于理想化,想作为、乱作为只能是帮倒忙!中国有13亿人口,需明白“众养则患、用之则昌”的哲理。过去搞计划经济由国家统包统揽,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边缘,若再大包大揽回到另一种形式的“大锅饭”上去,到头来恐怕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而财政再分配是政府的本份,通过深化改革更好发挥其“配置、分配与调节”的扛杆作用,政府责任重于泰山,改革作用牵一发而动全身!完善分税制改革,分三大财税区按“标准人”分配省级政府间地方财力。这里的“标准人”是指剔出统计常住人口中,诸如候鸟型农民工现象中的创造财富外溢或公共服务外溢后的真实常住人。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其户籍就业与外来就业人口负担率分别为1:1.6和1:1.03;也就是说按户籍每百位就业者需负担60个附加人口,而外来“新莞人”只需负担3个。这就说明外来劳动者为东莞创造了巨大财富而把附加人口负担大量留在了内地。按该市(2007)外来劳动力539万人占到总劳力83.5%来计算,当年共创造GDP2632亿元和出口额503亿美元;分行业测算创造财税收入396亿元占到了73.3%。但当年该市全部财政支出才185.45亿元。因此,同样是由于按财政供养人口计算地方财力,外来劳动者所创造的财税收入也不会很多留归当地,事实上接纳外来人口落户就会造成当地公共服务的外溢。可见,由于分税制尚未完全脱出原有财政承包制的窠臼,结果带来了普遍存在着的“劳动承接、户籍拒绝”的中国特有的候鸟型农民工现象。像解决此类发展起来的问题,显然必需改变这种按财政供养人口计算地方财力的传统作法。同时,对东莞市的情况还说明,如果不从年度统计人口中剔出各地创造财富外溢成份或公共服务外溢成份,直接按统计常住人口计算地方财力分配,看起来是与国际接轨其实不然,只有按剔出统计人口中劳动财富外溢或公共服务外溢的非真实因素后的“标准人”分配,才是实现国际惯例意义上的政府间真实常住人口的财力均衡。
记者:怎样实施统计常住人口的“标准人”分配?有没有什么依据?
张富泉: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这首先就应体现在财税制度的设计与管治过程中。里根政府开启全球性财政分权主义,就建立在“让每一个处于平等地位的人都得到平等的财政对待”的布坎南模型和联邦基本法的基点上;德国财政横向平衡制度的设计,其“假定各州人均消费水平基本相同”的理论,就来自其联盟基本法“保证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享有基本生活水准”的规定。按统计常住人口“标准人”分配,实质上是要按照“两个大局”战略转换的要求,基于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假定各省区市人的能力和努力程度的平均水平以及外部环境包括公共服务等条件相同。应当说,这种设计理念与方案,既借鉴了布坎南模型和德国财政横向平衡制度的成功之处,又体现了中国式的法治特色,也是从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与科学发展观完美结合的逻辑推论和精确计算得出来的。“标准人”分配模型的理论设计与推演过程,具体可见《邓小平战略设计:共同发展富裕的中国定律》的第四、第五章。它既体现了法治的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特点,又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显著不同。这一方案经实证分析易于操作且能广为接受,完全能够达致公平和效率有机结合、相得益彰的预期。不过,实行这种与国际接轨的统计常住人口的“标准人”分配,如上所述由于地方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发展竞争的中国特色,决不能照搬西方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分税制,而只能选择在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横向趋同俱乐部条件下,分别实行各个区域内省区市政府间财政横向均衡的制度。
记者:这样构建沿海连接内地的三大财税区,沿海与内地绑到一块是不是新的平均主义?沿海经济发达区会干吗?
张富泉:改革开放就是打破平均主义。邓小平向来反对搞平均主义,他说“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势必导致共同贫穷。”然而,构建沿海帮助内地共同发展富裕的经济区,沿海省市同样有着强烈的愿望。比如,广东省在2003年就提出构建“9+2”经济区的设想,最先打出了泛珠三角的概念。因为共同发展富裕不是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定律。在邓小平看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两条都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种本质论思想也完整体现在“两个大局”的改革开放战略中。沿海第一个大局战略的实施,是在改革初期效率问题成为主要矛盾时,让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发展起来,是要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转到内地第二个大局战略上来,构建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横向区域发展新格局,则是要突出沿海帮助内地共同发展富裕的主题。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达到小康后,沿海面临的已是新的发展问题,而内地仍然是脱贫致富问题,沿海与内地谁也不能离开谁。这种相互需求、相得益彰的损荣关系在新的发展阶段尤显突出。如果“两个大局”战略转换迟迟不能到位,长期徘徊于非均衡区域市场分割状态,沿海是沿海,内地是内地,就谈不上沿海帮助内地发展,那样沿海既帮不了内地也拯救不了自己。因为不能带动中西部内地共同发展富裕,则意味着巨大的内需市场和消费力不能释放出来,那么过多倚重出口拉动的沿海经济始终是不稳靠的。像遭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一旦出口受阻,其发展受到最大局限、受阻受损最大的是沿海而不是内地。因此沿海帮助内地也在帮助自己,不失时机地推进“两个大局”战略转换以实现共同发展与富裕,不仅是内地加快发展、缩小差距和公平正义的迫切要求,也是沿海拓展内需、优化结构和提升发展的内在需要。
尤其是在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财税区内,分别按统计常住人口“标准人”分配,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仍然是各省拿各省自己该拿的,并不存在谁占谁的问题。以相邻的广东、湖南两省为例,剔除按常住人口统计带来的劳动财富外溢或公共服务外溢的非真实因素,湖南常住人口(2007)“标准人”系数为1,则广东省(2007)“标准人”系数为1.542。也就是说在泛珠三角财税区当年财力分配中,按统计常住人口计广东人均财力为湖南的1.542倍。相应地其统计常住人口“标准人”系数高,则保增长和财政增收的压力也要大。同样以广东省为例,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GDP增速比上年下降了1/3,其统计常住人口也少增加了20万人,相应地其“标准人”系数下降到1.426(湖南系数仍为1),当年“标准人”结算财力比按上年“标准人”预分配财力需减少234亿元,相当于其当年结算可用财力的1.8%。
记者:这种“标准人”公式化分配的结果,能够剔除按常住人口统计带来的劳动财富外溢或公共服务外溢等因素,既能体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也对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人口自由流动产生了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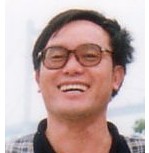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