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富泉:对!因为沿海和内地经济互补性极强,构建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财税区,实质上也是拓展区域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这样造就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机制,空间结构布局将从根本上得到优化,还能带来巨大宏观经济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沿海三大城市群按流域、地域连接三大内地带,无论哪个财税区都将远远大于1+1的收益。因此,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分税制体制,按统计常住人口的“标准人”公式化分配,各省“谁也不占谁”但谁都会比过去拿得多。沿海和内地只要算细账、算大账,就决不会有不乐意的。比如,不再按财政供养人口计算地方财力,改为按统计常住人口“标准人”分配,人口居住哪里就能把财政公共服务带到哪里,农民入城既能把本区域蛋糕做大,又能增加当地常住人口让蛋糕分得更多,这样长期困扰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再如,钱正英总结治沙经验是“人进沙进、人退沙退”,通过完善分税制理顺沿海和内地财政关系,让“以脚投票”的规律发生作用,中西部生态脆弱地区迁移出部分人口,生态安全和彻底脱贫也不再成其问题。而就沿海经济发达区来看,只要经济要素有序流动起来,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都有可能发展为上亿人口的现代化大都市,使我们的综合国力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记者:总书记讲话指出“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实现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开放。抓住完善分税制改革这个牛鼻子,是否能够打破利益分割格局,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
张富泉:如果说过来的财政承包制与分税制,是建立在东、中、西纵向非均衡区域与省级财政体非均衡竞争的基点上;那么新形势下完善的分税制,就必须构建在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横向均衡性区域与区域财政横向均衡的基石上。这三大横向财税区的“均衡三角”,可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力之所在。因为市场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公平竞争,由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市场经济竞争,这就需与企业、个体竞争者同样具备公平的起点。而在东、中、西纵向区域条件下省级财政体的竞争,各个省级区域发展基础与条件相差悬殊,如同奥运会与残奥会同台竞技只会造成混乱失序的状态。这一方面,各个省级财政体出于地方利益的刚性,加之区域差异与非均衡势必导致普遍的市场分割,难以实现全国市场统一;另一方面,经济越发达区际差距就越大,为抑制和缩小这种差距,只能动用越来越多的行政干预措施,结果市场化改革距离市场越来越远。“反过来”转向沿海帮助内地共同发展富裕的第二个大局战略,合纵连横形成区域财政横向均衡的三大财税区,这样重塑区域经济平等竞争的主体,东、中、西区际间越来越大的地区差距,将被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横向区域均衡发展所取代;现有省级为主的市场利益分割的格局被打破,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得以最终形成;市场规范相应带来行政行为的规范,将从根本上防止和避免权力寻租与腐败现象的发生;加之趋同俱乐部区域构成江河上下游生态贡献区与受益区的统一财政体,十分有利于类型区有序开发的统筹协调和生态环保等,将从根本上解决差距拉大、市场分割、贪腐滋生、生态恶化和社会公平正义等区域经济社会问题。同时,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这一“均衡三角”,还是一种天然的经济民主制衡机制,能够强有力地促进央地政府职能分开。
记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够职能分开吗?
张富泉:不仅能够分开而且必须完全彻底分开。因为市场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公平竞争,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就不可能有公平竞争。解决的办法,就是央地政府职能彻底分开。地方政府尽可能多地退出甚至完全退出经济监管领域,主要致力于区域经济发展与市场公平竞争。中央政府及垂直部门只起“守夜人”作用,维护好区域、企业、个体等市场主体成员的平等地位、等价交换规则和公平竞争秩序。马克思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作过全面考察后,提出通过起点的公平以及规则的公平而达致终点的公平,并认为规则公平实际上是对起点公平的必要补充(毛程连等,2003)。有了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这组趋同俱乐部区域公平竞争的起点,确保其竞争规则与过程公平则成为完善分税制必需的制度保证。因此,中央政府“守夜人”的首务之责,就是对三大财税区在立项、用地、财税、金融等行政性资源配置上,必须严格实行“取之同等、予之等同”的原则,使之在其竞争公平的起点上确保竞争规则与过程的公平。
记者:光凭政府“守夜人”的觉悟,没有相应的制度约束恐怕还不行。怎样用适宜制度来保证区域竞争规则与过程的公平呢?
张富泉:这就势必要求规划体制的配套改革。一般情况下,越是适应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区域规划与政策,就越不适应于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战略。广而推之,从计划经济时代流行至今的规划和预算两个报告的分读体制,恐怕也不能不做出某种完善与改进。在这个方面,可借鉴德国由联邦财政部长牵头共同组成联邦财政计划委员会的作法,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由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牵头,央行与国土、劳动、环保等部门参与咨询,并吸收“均衡三角”各区域部分省区市代表参与,组建具有相当权威的国家总体规划加三大财税区规划即“1+3”规划统筹办,担负起统筹规划、制定预算、协调利益等重要职能。并将“1+3”规划的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作为一项重要议题落实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民主决策过程中,最终采取票决制予以审定,以强化“均衡三角”经济民主制衡机制的作用,最大限度地落实公平、公正、效率与理性的原则。基于“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的原理,人们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力,则意味着竞争起点公平;面对的是同一的投票规则,这就保证了规则的公平;加上在信息完全的假定下,结果就自然而然是公平的了(胡寄窗,1991)。显然,“两个大局”战略转换后的横向区域与区域财政横向均衡制度,由于其起点公平建构在趋同俱乐部区域“均衡三角”之上,而结果公平又体现在“标准人”均等化分配之中,存在的真实肯定比某种假定性设想要可靠得多;然而保证区域竞争规则与过程的公平,恐怕还离不开以上这种“同一的投票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实施“两个大局”战略转换形成的区域“均衡三角”,既是新形势下完善分税制的必要依托,又具备经济民主制衡的政治体制自愈机能。
记者:“均衡三角”的经济民主制衡机制,如何在运转中体现政治民主建设的自愈机能?
张富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经济民主制衡机制的形成,是为确保完善分税制条件下三大财税区公平有序地竞争。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的观点,民主宪政的本质与核心内容当为经济民主。正如村级基层民主建设成果所反映的,只要村务公开、有了透明度,村民就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民主(朱隽,2011)。可见受广大民众所拥戴的真正管用的民主还是经济民主。西方流行的政治制衡,七拐八弯最终还是落到经济制衡上,说到底还是为了解决政府失误和公权滥用问题。但不管怎样,都是秋后算账的一种事后纠错机制。而区域“均衡三角”经济民主制衡机制的形成,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出于本身基本经济权益的争取与维护,其区域机会均等、分配均衡和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所形成经济民主制衡的倒逼机制,直奔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公平与效率的主题,较之政治制衡应是一种事前纠错机制,完全能够更好实现民主政治与决策的高效率。
比如,有了这种“均衡三角”民主制衡机制,对“1+3”财政预算与发展规划的科学制定,首先就极具聪明智慧的挑战性。如果不能广纳博采、选贤任能和集中智慧,就不可能做出兼具效率与公平的聪明型成长方案来,而不具实际指导意义或三大财税区不能摆平或在某个区域内摆得不具比较效益的规划,都将遭到责难甚至难能通过。这就势必造就一种人才脱颖而出、创新与智慧迸发涌流的民主氛围时代。同样,不具参政议政代表能力者则意味着被代表方利益的受损等,都将起到激发人才辈出、强化经济民主机制的奠基作用。而对“1+3”规划的实施过程,“均衡三角”经济民主制衡机制又是全方位全程的监督,掌握着经济社会发展权、土地、资金调配权和财政大权的一些重权部门,都将倒过来被置于多方监督之下,起着广泛矫正行政行为和社会清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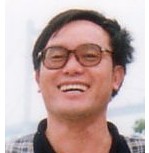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