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死刑无效:对腐败惩处的国际比较
长期以来,中国法律把腐败归为“经济犯罪”,包括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受严刑遏制犯罪的传统思想影响,中国法律对腐败的处罚和对金融欺诈、暴力犯罪等的处罚一样严厉。对腐败的严惩或许反映了中国对严重犯罪的严打政策,即强调通过迅速严厉的惩罚来打击犯罪而非预防犯罪。表1列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规定的对贪污罪的处罚。尽管《刑法》规定贪污数额不足5000元的可以被处以行政处分而非刑事处罚,但数额超过5万元的就会被判处五到十年的有期徒刑,甚至无期。此外,10万元以上的腐败行为就属严重犯罪。当然,随着近年来腐败涉案金额的不断上升,判处死刑的门槛也越来越高。那些被判处死刑的贪官通常受贿高达数百万甚至上亿元。
尽管法律在执行上显得宽松,近年来仍有5000多名官员被判处五年或以上有期徒刑,占被正式审理的经济犯罪案件的六分之一,占法院待审案件的四分之一。由于相关信息未公开,究竟有多少人因经济犯罪而被判死刑尚不清楚。然而,据估计在中国因腐败被判死刑的更多是级别较低的官员而非高官。政府有时也会对贪腐的高官施以重刑,以表明反腐不仅要打苍蝇,还要打老虎。1952年,在共产党执政仅三年后,党内的两名高官——刘青山和张子善,因在“三反”中的严重腐败而被执行死刑。自那以后,腐败在计划经济时代已不是政府要关注的重要问题。2000年,当腐败在经济改革时期变得普遍时,死刑在长达五十年之后第一次被施以一位高官——胡长清,江西省前副省长。自胡长清后,至少还有6位高官因为腐败而被执行死刑(成克杰、李真、王怀忠、郑筱萸、姜人杰、文强)。在过去的十年里,已有十几位高官被判处死缓,还有很多高官被判无期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如两位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和陈良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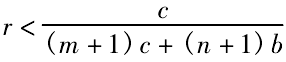
毫无疑问,官员因腐败而被判死刑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因此,大家普遍怀疑政府不过是象征性地保留对腐败处罚的这一极刑,主要还是为了表明其打击腐败的决心,平息公众对贪官的憎恨并赢得民众支持。然而,中国对腐败的刑罚还是很严厉的,尤其是与其他国家相比。如果用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CPI)来作为衡量腐败程度的指标,我们会发现很多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很少依靠重刑来控制腐败。在东亚,新加坡(2010年的CPI为9.3)被认为是世界上拥有廉洁政府的国家之一,但其对腐败官员的处罚通常是三年以下监禁或是10万新元以下的罚款,或者两类处罚并用。针对一些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监禁期会被延长至5年但最多也就7年。在日本(2010年的CPI为7.8),近年来的腐败程度相对较低,死刑不适用于腐败的公职人员,更为常用的处罚是罚款20万到100万日元,且五年内不得参加选举。即使有官员因腐败而被判刑,时间通常也就2年到5年,最多7年。在一些西方国家,比如美国(2010年的CPI为7.1),按照联邦法律,对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的处罚是降职或处以贪污受贿金额三倍以下的罚款(视哪一种处罚更重),或者是判处15年以下的监禁,抑或两类处罚并用,还有可能被免去在某些职位任职的资格。
即使在一些腐败严重的国家,其处罚力度也不似中国那般严厉。在墨西哥,其与中国的CPI值接近——大概为3.5,但该国对腐败官员的惩处既没有终身监禁也没有死刑。墨西哥联邦刑法典规定,对于情节轻微的腐败行为,如官员贪污受贿金额不超过该国最低日工资500倍的,将被处以三个月到两年的监禁,罚款额度为最低日工资的30倍到300倍,或者三个月到两年内不得在公共部门任职。贪污受贿数额超过最低日工资500倍的,则被处以2年到14年的监禁,罚款则是最低日工资的300倍到500倍,或是2年到14年内不得在公共部门任职。在蒙古,其2010年的CPI为2.7,但其对腐败的处罚也较轻,通常是一个月到5年的监禁,或者是经济处罚,数额为最低工资的5倍到250倍。在东亚,和中国一样对腐败惩处很严厉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但是该国的腐败问题也很严重,2010年的CPI为2.8。在印尼,对贪官处罚的最高监禁期长达20年。针对情节极为严重的腐败行为,也有可能施以死刑。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